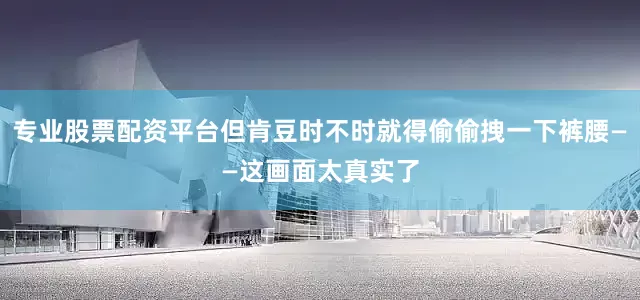——【·引子·】——
前言两千名贵族官员倒在了黄河岸边,一位出身于部落的将领在帝都的核心区域大开杀戒。鲜卑战神尔朱荣,用了三年时间,从边境逐步攀升到权力的顶峰,又在这三年里,把北魏推向了分裂的深渊。血腥屠戮朝堂,擅自立帝,兵权全掌,究竟是谋划已久的布局,还是一步步走向死亡的陷阱?故事就从六镇边疆开始说起。

边地出狠人,鲜卑铁骑崛起路
鲜卑部族素有战斗力强的名声,契胡部更是其中非常勇猛的一支。这位尔朱荣出身于这里,他既不是皇族,也不是世家子弟,在朝廷眼里就是个莽夫。不过,也正因为这种出身,让他比那些衣着光鲜的中原贵族更懂得刀兵的厉害。他不是通过科举崭露头角,而是一场场血腥的战争积累军功,逐步赢得了人心。

北魏的六镇表面看似还算稳固,可实际上内里早就暗流涌动。外族不断蚕食,加上赋税重得离谱,边疆将领还常常横征暴敛,最终引发了一系列的兵变。朝廷节节败退,六镇几乎快要失去控制。这对尔朱荣来说,倒不是啥危机,而是一大好机会。在动乱的时刻,他没急着参战,而是先稳住自己手下的军心,然后不断扩充兵力,等着其他部族和军头们为了争夺地盘打得天翻地覆时,他就低调观察,伺机而动。
别人争夺地盘,他就把人马扩充得更强。别人忙着要赏赐,他反倒专心训练骑兵。借助契胡部原有的基础,再加上一些投奔而来的六镇残部,尔朱荣很快组建出一支精锐的骑兵队伍。他不像南方那些将军依赖调动粮道,而是凭借山林和草原的条件养马放牧,一支队伍就像一支游牧战团,随时因素战场,跑得快,打得狠。

朝廷其实早就看清了他的崛起路径,只是不敢轻易动手。孝明帝一边努力镇压叛乱,一边还得提防宫廷内部的斗争,根本没有心思管那边的事。而尔朱荣又是个聪明人,他既不去挑战皇权,反倒屡次献策送粮、出兵平乱,顺势树立起一个“忠臣将军”的名声。
他真正崭露头角是在葛荣起事的那一年。葛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中原,一路攻城掠地,连皇上都觉得大厦摇摇欲坠。朝廷调不到有实力的部队,只得派出还算尚未成为“威胁”的尔朱荣去试探。这次机会,他可是等了很久呢。

在太行山前,尔朱荣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。他不像别人那样硬碰硬地迎战,而是采取了先切断补给,再攻占营地,最后围攻城池的策略。葛荣的部队虽人数不少,但队伍杂乱无章,战线拉得太长,经不起持久战考验。尔朱荣循序渐进,扎实推进,最终在一场战斗中击败了敌人,擒获了葛荣,将其头颅送到洛阳,震动了整个天下。
洛阳里都震住了,一个鲜卑边将,居然能一扫中原的叛军,几乎没咋损兵折将。百官们开始偷偷议论起这个新崛起的“战神”,民间也把他传为武圣。不过最紧张的,可不是敌人,而是皇帝和朝廷那些官员们。
此时的尔朱荣,不再是单纯的将军那么简单了,他掌管着北方的重要军政要地,手底下的将领全都由他提拔出来的。更关键的是,他没有再折返兵营,而是静静站在那里,等着皇帝的指令。实际上,他已经变成了个mini朝廷——有兵力,有资金,还有民心的支持,更别提那“平乱英雄”的名声了。

但他心里没焦虑。他清楚,要想推翻现有的皇帝,得先“清除朝中的忠臣”,要想掌握大权,得先制造“危机”。他就在等那个能让自己兵临洛阳,又不惹人指责的借口。这一幕,不用等太久就出现了——孝明帝去世了,那个只有三岁的幼皇帝被扶上了皇位,胡太后还在躺在帘幕后掌控大局,朝堂再次变得乱成一锅粥。
洛阳还没稳住局面,各地的军头就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。尔朱荣干脆直接派兵向南进攻,口号就一句:“清君侧”。一切都安排妥当,他想的,就是兵不血刃地攻入皇城。不过当他发现朝中还有人在抵抗,他就换了个策略。
下一步行动,肯定会彻底改写北魏的政体格局。

掀案河阴,屠刀落下官僚头
在黄河沿岸,洛阳城北方。四月时节,春寒依旧,但空气中已满是血腥味。尔朱荣的军队已占领城池,胡太后和年幼的皇帝元钊被掌控。没有象征性的软禁,也没有虚伪的“辅政”,他直接命令将两人投入黄河。这不是偷偷杀人,而是毫不遮掩地向天下宣告。
大家都明白了,这可不是普通的改组,而是一场彻底的清洗。权力从皇族那里流失,既不是悄无声息的,也不是轻轻松松的事,而是伴随着血流成河的残酷屠戮。

接着发生的“河阴之变”,可以说是一场针对朝廷的全面大屠杀。尔朱荣亲自安排指挥,提前列好了名单,把那些曾参与决策、反对过六镇改革的官员和贵族统统列进去。没有经过审讯,也没有流放,一律秒杀。
两千多位王公大臣、宗室子弟以及昔日的老臣,被集中到黄河边,统统处死得一干二净。有的人还穿着礼服走向断头台,有的人还没醒过来就被士兵拉走。没人曾料到,一个朝代的权贵阶层,竟然能在一夜之间被彻底清除得如此干干净净。
尸体堆满了河滩,血水流入了黄河。没人来收拾尸体,也没人敢哭泣。整个洛阳城陷入一片死寂,权贵区空无一人。民间纷纷传言“地狱之门已开”,但是没有人敢说清是谁开的这扇门。

血腥过后,尔朱荣也不隐瞒自己的目的,他声称这是“扫除奸佞”“稳固根基”,不过大家心里都清楚,现今的北魏,实际上已经由他一人掌控。
新皇帝由他亲自挑选,长乐王元子攸,这位没有什么深厚根底、容易驾控的傀儡。当他登上皇位的那一刻,身边只站满了鲜卑军将,没有官员的恭贺,也没有乐师的乐声,只有尔朱荣那冷峻的目光。

尔朱荣大概感受到出了点问题,可他也顾不得停下来,他调动更多兵马往长安、邺城去,要加强控制,甚至打算效仿秦汉的管辖方式,重新设置军区。认为只要用强硬的手段掌控住局势,皇权就不会反抗。
可是,他忽略了一件事——皇权最怕的,根本不是刀枪,而是被架空。孝庄帝虽然是他扶持起来的,但毕竟是个活的存在。他一边静静地积蓄力量,一边耐心等待,等尔朱荣露出破绽的那一刻。

权力高悬,皇权只剩空壳
河阴之变一过,洛阳再也没有宫殿里的朝廷,只有军营里的兵营。那些朝政的文件不再经过中书门下,而是直接由尔朱荣在军帐里签署。兵权、财权、人事权全部都汇聚到他手里,没有任何制约,也不用商量,搞得全北魏变成了他的私人军政府一般。
他不喜欢讲排场,也不建府邸,每天还是穿着戎装。城里人说他是“镇狱明王”,半神半魔,不仅能灭国,还能封侯。没有亲信谋士,只有几百名骑兵近身随从,驻扎在城北,昼夜不离身。城里的百姓看到他们出行,就像兵临城下,纷纷闭门不敢出。杀气太重,没人敢靠近。

老臣几乎都死光了,剩下的要么藏进庙里,要么装疯卖傻。新来的官员多是军人,基本不识字,但办事效率快得很。尔朱荣并不在意这些,他们只管听从指令。宦官制度被一扫而空,太学里空无一人,洛阳变得冷峻起来,也变得陌生。
他扶持的孝庄帝,也变得沉默寡言。早朝时,他就像个木偶似的,坐在那里等尔朱荣的汇报和指示,然后签字退朝。没有什么实权,连发言的份儿都没有。尔朱荣也不在意这些,连礼仪都不怎么讲究,进殿不用跪,回话也随意,整个朝堂变成了将军的营地似的。
各地都纷纷上书恭贺“清君侧”取得胜利,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明白,大家都提心吊胆。外镇的将领们都知道,这朝堂不再是他们熟悉的地方,兵权换了人,没人敢再自称忠臣。尔朱荣派出亲族担任监军、掌印,取代了以往的地方官,掌控粮道、边疆,一切都在从上到下悄然变动。

不过底层也传出一些不同的声音。来自六镇的兵士里,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尔朱荣心存感激,有的人家人在河阴遇难,有的被征调了好几年还没回来。他们怕他,但并不敬畏他。南北的交通逐渐中断,关中地区也爆发了一些小规模的骚乱。
尔朱荣明白啊,扩张是得坚持下去的事情,也得靠战争来巩固自己的势力。他调兵入关,让尔朱兆去攻打西北,还派世隆把持邺城。他以为只要行动迅速,外地的反抗就来不及反应。不过没料到,皇帝在暗地里早就布下了棋。
孝庄帝在宫里几乎哑口无言,但他借助乳母、老太监以及宫外的秘密渠道保持联系。他故意装作不反抗、不质疑,让尔朱荣放松警惕。心里明白,靠写奏章争夺权力是不可能的,唯一的办法就是一招致命,才有可能从这个“镇狱明王”手里夺回朝廷的控制权。
机会突然降临,没有预料到。尔朱荣的亲信请假回营,皇帝趁机布置了一场局。宫里传来皇后的生产消息,尔朱荣被邀请进宫去道贺,平时这种事也挺常见的,属于例行公事。但这次,他却没再出现。

血染明光殿,三年霸主一朝崩了权力的终点
公元530年冬天,尔朱荣准时去到宫里,穿着战甲还没脱掉,身边还跟着随从。皇宫对他一如既往,没有拦阻也没有检查,还安排了酒宴款待他。他一点警觉都没有,可能也觉得没必要再保持警惕了。
天色刚黑,皇帝就起身迎接,语气温和。几杯清酒喝完后,现场变得异常静谧。突然,一阵喊杀声从后殿传来,一队禁军紧随而至,刀光斧影,把金杯砸得粉碎。尔朱荣还没来得及拔刀,头就滚落了,元天穆也当场被杀。
宫人看了这一幕,忍不住都愣在原地,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尸体也没有人去传,说是皇帝下了秘葬的命令,没有哀乐,也不让外人知道。直到三天以后,这消息才传到洛阳,整个城市都像是炸了锅——不是因为悲伤,而是满满的恐惧和慌乱。

尔朱荣一死,问题可没就此解决。军队还驻扎在外头,他的亲族还掌握兵权,还有十几个尔朱体系下的地方督将还没有回来。孝庄帝没给他缓冲的时间,只能硬着头皮接下这烫手山芋。他派了新将去接管那些地方,试图清理残余势力,可动作太快太激烈,一下子反倒引起了更大的反弹。
尔朱兆一听到哥哥死了,就带兵南下,把洛阳给围了起来,声称要“讨贼报仇”。孝庄帝节节败退,不得不跑了出去。这回,尔朱家再一次掌握了政权,才几个月功夫,权力又回到军头手里了。

这回情况不一样啦。尔朱荣还算有点名望,有些功劳,又有点主心骨。反倒是尔朱兆他们,只会抢地、打仗,没啥治理的本事。各地将领趁机自立门户,不再听从皇命。朝廷变成了战场,皇帝也成了流亡的逃亡者,北魏完全分裂开来了。
一年过去了,尔朱兆败给了高欢,战败身亡,尔朱家族的势力也全都崩溃了。北魏皇族接连更换,最终分裂成东西两魏,整个国家的格局彻底碎成了零散的碎片。
大家开始议论纷纷,若尔朱荣没死,或许还能稳住局势,也许还能再“清君侧”一次。不过,这些都不再重要了。他像一场席卷一切的风暴,瞬间扫荡一空,把整个帝国都连根拔起。
三年的权势换来了一世的恶名,江湖上人们一直记得的,是黄河边那两千条人命,是明光殿那一刀的惨烈场景,更有人说北魏从帝制转向军阀割据的转折点,莫不过如此。而尔朱荣的名字,也就这样,被锚在了历史最沉重的一页上。
富灯网配资-配资查询114-海口股票配资平台-股票配资实盘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